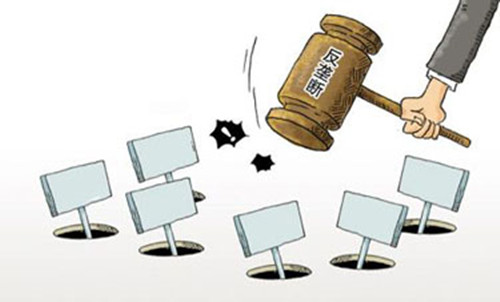2016年11月16日,工商总局结束了对瑞典著名包装企业利乐公司历时近5年的反垄断执法调查。据工商总局调查,利乐滥用其在纸基无菌包装设备、服务技术和包装材料市场的支配地位,搭售包装材料、限制上游供货商与其竞争对手交易、实施忠诚折扣,排挤竞争对手,妨碍有效竞争。对此,利乐公司于同日声明接受约6.67亿元人民币的处罚,不再寻求行政复议或诉讼。
利乐案是目前为止,我国竞争法历史上,办案周期最长的案件,至少可以追溯到2004年工商总局根据举报委托学者调查食品饮料包装行业。当时,由于我国还没有《反垄断法》,难以从限制竞争的角度调查利乐。其后,利乐都没有因2008年8月1日《反垄断法》生效而停止实施涉嫌违反该法的搭售行为,而同样的行为早在1991年就已在利乐的大本营——欧洲市场被认定违反欧共同竞争法。
不过,当工商总局在2010年12月31日正式通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定》细化《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后,利乐也随之在2011年停止了这种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的搭售模式,取消了对上游包装纸厂家向竞争对手出售原材料的限制,放弃了产业经济学教程中常见的“客户封锁”、“原材料封锁”。
换言之,如果《反垄断法》早在2004年就颁布实施,又或在2008年生效时,就能有细化该法的配套规则落地,那么利乐很可能会从自身合规角度考虑,在12年前,或8年前就自行终止上述两类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这样的例子在国内并不少见。而这也就意味着,2011年后国内不少行业扭曲的竞争格局恰恰是因为《反垄断法》颁布过迟,配套规则没能及时颁布所致。
处罚虽然是来晚了,但利乐公司还是没能躲过处罚。而处罚的法律依据源于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在违法行为终了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而没能像欧盟那样,把处罚违法行为的追溯时效延长为五年。利乐在2011年刚停止上述两类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就在2012年1月被工商总局正式立案调查,没能挨过行政处罚的两年追究时效;另一方面是因为其在2009年至2013年还实施了《反垄断法》配套规则没有明确列举禁止的忠诚折扣,产生了排挤竞争的后果,“出乎意料之外”地被工商总局适用该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兜底条款予以禁止,尽管2009年欧盟委员会对英特尔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忠诚折扣行为处罚10.6亿欧元的前车之鉴早已为全球制造业所公知。
尽管利乐公司最终被处罚6.67亿元,但与欧盟国家相比,我国的惩罚力度并不大。
长期以来发改委和工商系统的反垄断执法者在适用《反垄断法》第四十六条、四十七条计算罚款时,都对法条采取限缩性解释,把罚款总额限定在“立案前一年”经营者“实施具体违法行为的子公司、分公司”“所涉业务销售额”的1%至10%之间,且往往动辄就给配合执法的经营者按罚款上限的“3折”到“1折”从轻处罚,导致违法成本极低,无法惩前毖后、以儆效尤。相比之下,我国《反垄断法》所参考的欧盟竞争法则与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以“处罚决定做出前一年”“违法者所属企业集团”“在全球的全部销售额”的10%作为罚款上限,以违法行为持续时间长短、造成危害的具体情况来确定最终的罚款,通过覆盖违法行为可能带来的全部收益,达到让违法者得不偿失的执法效果,即便是当事人配合执法也只能依法最多减轻10%的罚款(限制竞争协议中主动自首的情况除外)。
由于我国反垄断执法实践在罚款计算上存在上述严重的弊端,导致违法成本低,可以“讲价”的余地大,也就难免会让利乐公司缺少积极配合工商总局在短期内结束调查的动力。而且,因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习惯于按“立案前一年”违法行为所涉销售额作为罚款计算的基数,以至于利乐管理层在被立案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框定了罚款上限”,无需担心调查可能对未来业绩考核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自然也就会缺乏配合执法的紧迫感。
更重要的是,在调查结束之前,利乐仍在实施的忠诚折扣行为尚未被依法禁止,仍可以在调查期间继续帮助利乐巩固市场支配地位,获取垄断利润。而这难免会诱使利乐公司采取“拖字诀”,以行使程序权利为由,与本身人手不足、岗位流动性大的工商总局反垄断执法专案组周旋,拖延调查进程。
最终,在调查持续近五年后,利乐公司转变风格,表示“遗憾”地接受工商总局的处罚,既不上诉也不复议。这不排除是因为今年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委托国家发改委起草了《关于认定经营者垄断行为违法所得和确定罚款的指南》(征求意见稿)。该征求意见稿虽然仍没能改变上述限缩性解释法条致使行政处罚孱弱的局面。但是,其笼统地提及了反垄断执法机构计算违法所得的方案,并为执法机构是否没收违法所得、如何计算违法所得赋予了缺少法定公开程序有效监督的巨大自由裁量权。
而相比发改委系统反垄断执法实践中鲜有没收违法所得的情况,在利乐案之前,已公布的41个工商系统反垄断执法案件中有12个案件都没收了违法所得。这种对违法者没收违法所得的趋势在2016年已成为工商系统反垄断执法的常态。
因此,对于利乐公司而言,接受工商总局对其中国子公司在2011年相关销售额7%的罚款,显然远远好过拖到“被没收违法所得”的那一天。
工商总局对利乐做出的47页处罚决定让外界对我国反垄断执法工作的质量产生更高的期许与要求。然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很可能是比利乐案更加棘手、难度或阻力更大的案件,例如:2014年工商总局对微软的调查,2015年“双11”根据京东的举报委托浙江省工商局对阿里巴巴的调查,类似信雅达等划分市场案那样有行政机关参与的垄断协议,以及不久的将来依据国家发改委牵头起草的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汽车业的反垄断指南》规范汽车业的限制竞争行为。
这样的荆途也同样是地方反垄断执法机构要面临的。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考核监督与激励机制,许多地方反垄断执法机构至今仍因人才储备不足、专业培训缺乏、怕得罪人、怕麻烦、怕影响地方经济、缺乏上级领导和地市县级政府的支持,而没有动力调查本辖区的限制竞争行为,为国内外批评我国反垄断执法机关选择性执法留下口实。据笔者统计,《反垄断法》生效8年来,至今仍有15个省级工商局(黑龙江、吉林、河北、北京、天津、上海、福建、广西、贵州、西藏、青海、新疆、甘肃、陕西、山西)扮演“唤不醒的装睡者”,在反垄断执法上交白卷。
在这样的荆途上,倘若换个角度积极地看:无论是在全国市场,还是在地方市场被调查的企业,无论是因涉嫌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被工商、发改委系统调查的企业,还是未依法申报就实施经营者集中的滴滴、携程等互联网经济的宠儿以及它们的竞争对手们,客观上也都可以通过举报违法行为、配合执法、积极申辩、参加公开的听证程序,与反垄断执法机构一道成为厘清《反垄断法》适用、推动反垄断法配套规则完善、梳理本行业竞争规范、重塑有效竞争格局的推动者。在利乐案中,多年来一直能坚持举报利乐违反《反垄断法》,并给予执法者足够信任的企业便是很好的榜样。